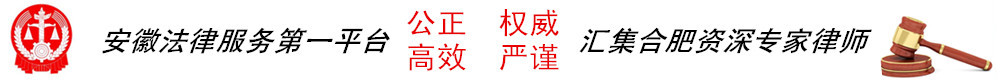某钢铁公司(2009年2月27日更名为甲集团)与乙公司于1996年9月在某市注册成立渡假村公司,注册资本6601.9万元。其中乙公司出资3961.14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60%,甲公司出资2640.76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40%。2002年11月渡假村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扩股后渡假村公司的总股本为16291.89万元,其中乙公司出资8097.13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49.70%;甲公司出资5424.76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33.30%;丙公司出资150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9.21%;丁公司出资64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3.93%;戊出资25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1.53%;己公司出资380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2.33%。2006年2月,丙公司将其持有的9.21%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庚公司。
2006年11月9日,渡假村公司董事会向各股东致函,要求各股东针对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的合作开发事项进行表决,并将表决结果于2006年11月15日前发送至董事会指定的传真号或邮箱。渡假村公司的六家股东除丁公司弃权未表决外,其余五家股东均向渡假村公司董事会送达了表决意见。其中乙公司、丙公司、己公司投赞成票,以上三家股东共持有61.24%的股份;甲公司、戊投反对票,以上两家股东共持有34.83%的股份。根据这一表决结果,形成了《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了渡假村公司和A公司的合作开发方案。该决议落款为“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周某”,并加盖渡假村公司公章。
2006年11月28日,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签订《B市度假村合作开发协议》及《备忘录》,双方又于2007年5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及第二份《备忘录》。以上协议约定渡假村公司将其70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和开发权交给A公司,作价8033万元;A公司向渡假村公司支付7181万元用于渡假村公司在另一块23.9亩土地上建造约12000平方米的四星级酒店;A公司为渡假村公司职工解决213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按每平方米4000元计算以及将1350万元用于职工房改安置补偿款一次性付给渡假村公司,由渡假村公司分别付给职工个人。A公司按此约定共计应向渡假村公司支付9383万元。双方还约定如有一方违约,除应赔偿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外,还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其后,渡假村公司和A公司前期合作相互配合,A公司将职工宿舍建成(但尚未交付使用)并支付渡假村公司职工补偿款1350万元,为渡假村公司兴建的四星级酒店支付工程款4111.926614万元。但从2008年3月开始,双方因渡假村公司应过户给A公司的70亩土地是否符合土地转让条件,能否办理项目变更手续等问题产生分歧,于2008年6月和8月分别提起诉讼。其后,对于渡假村公司提起的(2009)B市民一(重)初字第3号案,B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对于A公司提起的(2009)B市民一(重)初字第2号案,B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渡假村公司将位于B市渡假村内的“B市湾国际公馆”1、2号楼项目及其占有的70.26亩土地使用权过户到A公司的名下,渡假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万。渡假村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0年12月24日作出(2010)琼民一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驳回渡假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B市湾国际公馆”1、2号楼项目及其占有的70.26亩土地使用权已于该案判决前先予执行过户到A公司名下,渡假村公司尚未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
甲集团曾于2009年4月28日向乙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乙公司与其协商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乙公司分别于2010年4月2日和9月28日向甲集团发(回)函称,就股东权益问题待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的诉讼有了结论后双方再协商处理办法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法院另查明:甲公司于2007年1月向B市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渡假村公司2006年11月17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并撤销该决议。该院于2007年7月9日作出(2007)城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判令撤销2006年11月17日的《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渡假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B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5日作出(2007)B市民二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B市市城郊人民法院重审。甲集团于2011年12月26日向B市市城郊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11年12月28日裁定准许甲集团撤回起诉。
甲集团认为由于乙公司不顾其他股东的反对意见,决定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合作,导致渡假村公司数亿元的损失,其中甲集团损失2.344亿元,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1、认定乙公司在通过2006年11月17日的《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过程中滥用股东权利;2、判令乙公司赔偿甲集团经济损失2.344亿元人民币或者赔偿甲集团同类地段同类价格同等数量的土地使用权(21.3亩);3、判令乙公司赔偿甲集团因渡假村公司支付A公司100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产生的333万元人民币损失;4、判令乙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在2006年11月17日《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中,乙公司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的问题。2006年11月17日,乙公司要求股东对渡假村公司和A公司土地开发合作事宜进行表决,其中持有61.24%股份的股东赞成,持34.83%股份的股东投了反对票,其他股东弃权,未达到我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所规定的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乙公司利用其董事长周某同时为渡假村公司董事长的条件和掌管渡假村公司公章的权力自行制作《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系滥用股东权利,并由此侵犯了甲集团的合法权益。
二审法院经审理对于乙公司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并由此给甲集团造成损失的问题,认定如下:
2006年10月22日,渡假村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了该公司与A公司合作开发事宜,并决定于同年11月7日之前全体股东就该事项进行书面表决。此后,公司的股东按照董事会要求进行了书面表决,其结果为:包括乙公司在内的三家股东赞成,甲集团等两家股东反对,另有一家股东(单位)弃权。同年11月17日,渡假村公司董事会作出《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布了表决结果,其称股东会以61.24%的赞成票通过了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的合作开发方案。该文落款为“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周某”,并加盖了渡假村公司的公章。其后,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相继签订了《B市度假村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等协议,并实施了合作开发事项。法院认为,在渡假村公司股东会进行上述表决过程中,乙公司作为该公司的股东投了赞成票,系正当行使其依法享有表决权的行为,该表决行为并不构成对其他股东权利及利益的侵害。基于全体股东的表决结果,渡假村公司董事会制定了《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载明:“根据公司法规定:渡假村公司股东会通过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合作开发方案。”此后,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并将之付诸实施。这些行为及经营活动均是以“渡假村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名义而实施,其对内为董事会行使职权,对外则代表了“渡假村公司”的法人行为,没有证据证明是乙公司作为股东而实施的越权行为。尽管大股东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某同时担任渡假村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但此“双重职务身份”并不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且该董事长系由渡假村公司股东会依公司章程规定选举产生,符合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此情形下,渡假村公司及其股东乙公司均为人格独立的公司法人,不应仅以两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自然人,便认定两公司的人格合一,进而将渡假村公司董事会的行为认定为乙公司的行为,这势必造成公司法人内部决策机制及与其法人单位股东在人格关系上的混乱。此外,两公司人格独立还表现为其财产状况的独立和明晰,在没有证据证明公司与其股东之间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下,此类“董事长同一”并不自然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原理”中的“人格混同”之情形,不能据此得出乙公司的表决行为损害了渡假村公司及其股东甲集团利益的结论。因此,原审判决依“乙公司利用其董事长周某同时为渡假村公司董事长的条件和掌管渡假村公司公章的权力自行制作《B市渡假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认定乙公司“系滥用股东权利,并由此侵犯了甲集团的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中渡假村公司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的合法性与乙公司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渡假村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八条第(6)项“议事规则”规定“股东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股东会的决议,修改章程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二审期间,甲集团、乙公司对该条款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是否适用本案的表决存有不同理解。即“股东会的决议”是指股东会的所有决议,还是仅指关于“修改章程”的决议。法院认为,该争议问题涉及股东会表决程序及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无论其合法性如何认定,亦都是渡假村公司董事会行使职权的行为,其责任归于董事会,而不应作为判定乙公司在表决中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的依据。此外,本案“土地开发合作事宜”属于该公司一般性的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并未规定该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故原审认定股东会就土地开发合作事宜进行的表决未达到该条规定的表决权不当。
关于甲集团所主张损失的性质问题。甲集团诉称,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合作开发项目中,其对土地价格的评估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给渡假村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其持有的股权比例,请求乙公司赔偿甲集团同类地段同类价格同等数量(23.4亩)的土地使用权。法院认为,甲集团诉称的“损失”产生于渡假村公司与A公司合作开发建设过程中,依双方约定,渡假村公司拿出部分土地给A公司开发建设,A公司则为渡假村公司建设一幢四星级酒店及职工宿舍等。甲集团据此主张由乙公司赔偿其相应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一、渡假村公司在该合作开发项目中的“损失”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法院在此不能作出判定;二、即使该“损失”存在,请求该项“损失”救济的权利人应是渡假村公司,而非甲集团;三、如甲集团代渡假村公司主张权利,则诉讼权利受益人仍是渡假村公司,这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